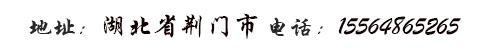对话艺文志品牌主理人肖海鸥书自有命,不复
|
0上海书展期间,新闻晨报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开展了系列主题直播,独家对话集团中5位具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主理人。作为“最懂书的人”,他们从不同视角向读者分享了各自的书籍出版心得以及对行业现状的思考。 本期嘉宾肖海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品牌主理人。艺文志品牌成立至今已有6年,出版超百本书籍,题材横跨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例如《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走出唯一真理观》《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本雅明传》《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等,本本精品,在豆瓣读书上鲜少有掉到8分以下的作品。 入行十二年,肖海鸥从编辑到叠加上“品牌主理人”这一身份和责任,她带领“人来人往”最多也只有5人的艺文志团队持续为读者带来好书,每本书收获好口碑的同时几乎都能实现加印,在本届上海书展上也准备了《山中》《书自有命》《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等新书带给大家。 艺文志的品牌故事,编辑工作的苦与乐,阅读习惯的变化冲击,出版行业越来越卷的营销卖书……一直坚信“书自有它的命运”的感性80后编辑肖海鸥,坦诚地将自身经历和对编辑、阅读的理解娓娓道来。 编辑的命运晨报记者:艺文志这个出版品牌是如何成立的?肖海鸥:我觉得好多故事都是事后追加的,它是非常偶然的,好像一切好东西也都来自偶然。有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当时我的老社长陈徵说,也许我们可以来试着做一个工作室,出版编辑们习惯擅长或是用自己的判断力做的选题。因为工作室其实和任何一个编辑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有文学编辑师,还有理论编辑师,只不过加了一个名字。艺文志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在不同的场合试着去解释它,因为大家都觉得任何一个品牌名字都有它的深意,其实完全没有,它就是“饮水思源”,非常自然地脱胎于我们文艺社,“文艺”到“艺文”很自然的联想。 晨报记者:艺文志品牌的书籍题材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仅是文艺,这是否也与编辑的兴趣和偏好有关?肖海鸥:我以前一直有一个非常深的“成见”,就是一个人如果兴趣非常繁杂,他就特别适合来做编辑。来做编辑的人肯定是喜欢阅读的人,他很可能是在硕士阶段甚至是博士阶段,在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割舍不掉一些兴趣,促使大家包括我来从事编辑这一行。 所以我会思考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艺文志的编辑,他们是否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抱有好奇?哲学、历史、文学、人文思想各个方面他可能都有兴趣,那么他很适合做我们的伙伴,但我现在也会反省这样的道路是不是健康或者可持续的,因为编辑如果涉猎非常广的话,会给自己加重无数负担,因为你总想把每一本书都做得很好,意味着你做一个新的东西你要投入,你就像面对一片莽荒之地,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走那条路,相比很多专注在一个赛道或者一个产品线的编辑,我觉得我们的道路要难很多,但同时也有趣很多。 编有些书会很愉快轻松,把自己全部阅读经历和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全部调动出来就可以了,但也有让我反省这样的选择是否合理,感受到巨大挑战与困难的时刻。 比如前两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我心虚到临时去报了一个日语课,虽然我大学学过一点日语,但那完全入不敷出不够用。 打个比方,就像令狐冲学剑宗跟气宗,我们就是剑宗一路摸爬滚打,不像饱学之士处理书稿那么从容,我都是现学现用到处找人问问题,以确保我们能做得准确。因为我觉得准确是书的第一要务,是编辑专业的体现,书的可信度完全建立在它是否能够更准确,也就是对真的追求上。 晨报记者:很多人好奇出版人、编辑是一份怎样的职业,也有很多年轻人想要进入这一行,你如何解读这个职业?肖海鸥: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进入这一行非常偶然,当时也不是我的家庭特别支持的一个选择,但它一直深藏在我心里,是一份梦想中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就是读书。 随着从业时间越来越久,我对这份工作的认同感会发生很多变化,我觉得认同感变化最大是在年,之前很快度过了蜜月期,然后你就要学习,要处理很多陌生事务,而且也许没有人教你,但又不能放低自己的目标,当你想做好的时候就非常考验你和这份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遇到好多年轻的编辑,他们都带着满腔的热情而来,但是可能我们始终无法提供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很快热情会被磨损,很多人也会伤心疲惫地离开,而我坚持下来,是因为书本身真的馈赠了我们很多,你心甘情愿为这一部分的馈赠去做无数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有人说图书编辑特别像保姆,编辑带着作者,然后等一本书出来再一字一字地看它,赋予它形式,然后再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特别像抚养孩子的过程。 对于我们来说,最深的吸引依然是这份工作里面最美好的部分,你愿意去读一个作者,你觉得那是人和人之间最美好关系的发生。因为你做了这本书,无数读者会读到这本书,也许对他的生命会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段奇遇都是因为你的工作,这些玄而又玄美丽让人沉醉的部分,把我们留在了这份工作里。 晨报记者:经常会看到怀有满腔热爱的编辑最终又离开了这个行业,是否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现在对于编辑有哪些要求?肖海鸥:今天对一个编辑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包括对人能力和心性的要求,对精力的要求是如此之高,但仅仅从世俗层面来讲回报是无法匹配的。 对于编辑的要求,在我这个阶段我觉得会是好奇,因为明显感觉到我做了1年编辑后,对世界的好奇正处在一个渐渐收缩的阶段,这是非常致命的,我一旦意识到就会警铃大作,因为这是不可以的,这意味着你无法再用你的触觉去感受到读者需要什么。 对其他更年轻的编辑来说,我会觉得是责任感。我常常为这种责任感所带来的深深内疚所折磨,但我又觉得好像是这份责任感在推动人们去完成那些工作。 责任感来自于会一直思考是不是把这本书做到位了,疑问是否真的解决了,读者阅读感受如何,如何在作者所要彰显的个性和市场预期之间找到平衡等等,这些判断都是每一个编辑要负责去做的,我觉得这份责任很沉重。 阅读的命运晨报记者:现在读者读书从读纸质书到电子书再到现在流行的听书,你如何理解这几年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肖海鸥:说实话这些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们靠纸质书营生,但我包里带着阅读器,走在路上会听书,今年年初上班通勤路上我就听完了《荷马史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当时有一种窃喜,我就觉得好多你曾经不可能读完的书,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读完。 像这些以前特别难读下去的书,我会选择用听的方式,因为它的时间流声音推动着你向前,你不得不跟随着它,就像有一个火箭助推器迫使你完成。 我拥抱这些新技术和新习惯,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媒介,重要的是你在读什么,你在听什么。我常常会想,我们出版什么书才是重要的,我们是否提供了值得用有限生命里的时间去阅读的书籍,而我们给大家提供什么决定了书籍的命运,决定了这个行业是否还被大家需要,我们还能不能生存下去。 晨报记者:技术发展带来的阅读习惯变化给出版行业带来了很多冲击,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肖海鸥:这是全行业都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anjizeiou.com/njzozl/12430.html
- 上一篇文章: 小型车智能新高度比亚迪海鸥非常鸥克
- 下一篇文章: 寄居蟹可以晒太阳吗